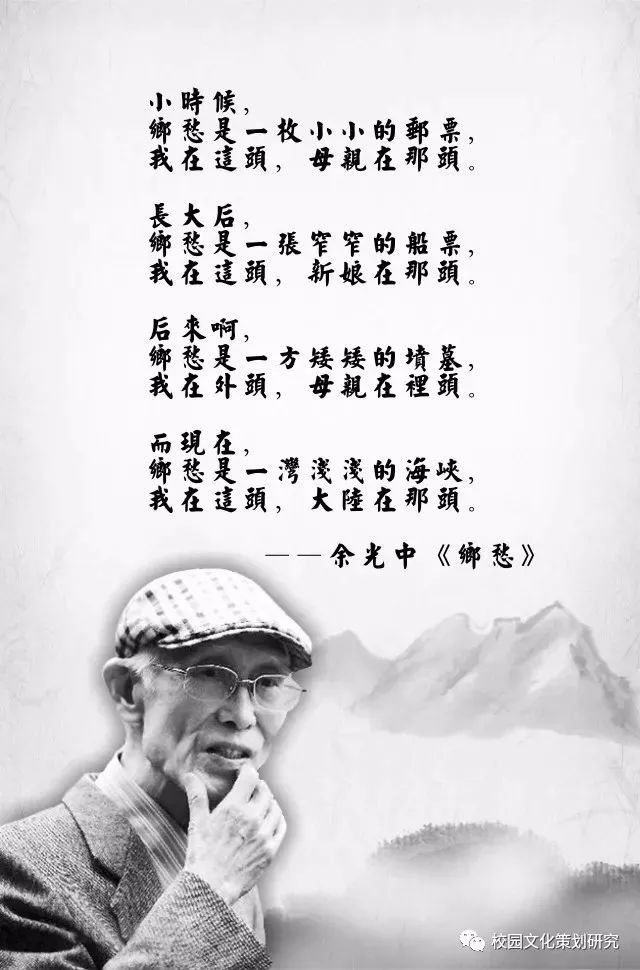5
青中的良師不少�,孫良驥老師尤其是良中之良。他是我們的教務(wù)主任�,更是吃重的英文老師,教學(xué)十分認(rèn)真,用功的學(xué)生敬之��,偷懶的學(xué)生畏之���,我則敬之�����、愛之���,也有三分畏之。他畢業(yè)于金陵大學(xué)外文系����,深諳英文文法,發(fā)音則清晰而又洪亮���,他教的課你要是還聽不明白�����,就只能怪自己笨了���。從初一到高三����,我的英文全是他教的��,從啟蒙到奠基����,從發(fā)音����、文法到修辭,都受益良多��。當(dāng)日如果沒有這位嚴(yán)師�����,日后我大概還會(huì)做作家�����,至于學(xué)者���,恐怕就無緣了����。
孫老師身高不滿五尺,才三十多歲���,竟已禿頂了����。中學(xué)生最欠口德�,背后總喜歡給老師取綽號,很自然稱他“孫光頭”�����。我從不符合他們�����,就算在背后也不愿以此稱呼���?��?墒橇硪环矫妫瑢O老師臉色紅潤�����,精神飽滿,步伐敏捷�,說起話來雖然帶點(diǎn)南京腔調(diào),卻音量充沛���,句讀分明����。他和我都是四川本地同學(xué)所謂的“下江人”�����,意即長江下游來的外省人��,更俚俗的說法便是“腳底下得人”��。我到底是小孩���,入川不久就已一口巴腔蜀調(diào),可以亂真���,所以同學(xué)初識����,總會(huì)問我:“你是哪一縣來的?”原則上當(dāng)然已斷定我是四川人了�。孫老師卻學(xué)不來川語,第一次來我們班上課�����,點(diǎn)到侯遠(yuǎn)貴的名�����,無人答應(yīng)����,顯然遲到了。他再點(diǎn)一次����,旁座的同學(xué)說:“他耍一下兒就來。”孫老師不悅����,說:“都上課了,怎么還在玩耍���?”全班都笑起來�����,因?yàn)?ldquo;耍一下兒”只是“等一下”的意思���。
班上有位同學(xué)名叫石國璽�,古文根柢很好��,說話愛“拗文言”����,有“老夫子”之稱。有一次他居然問孫老師���,“‘目’英文怎么說?”孫老師說�����,“英文叫做wood�。”有同學(xué)知道他又在“拗文言”了,便對孫老師解釋�����,“他不是問‘木頭’,是問‘眼睛’怎么說�����。”全班大笑���。
在孫老師的熏陶下���,我的英文程度進(jìn)步很快,到了高二那年���,竟然就自己讀起蘭姆的《莎氏樂府本事》(Charles Lamb:Tales from Shakespeare)來了�����。我立刻發(fā)現(xiàn)�,英國文學(xué)之門已為我開啟一條縫隙����,里面的寶藏隱約在望。幾乎,每天我都要朗讀一小時(shí)英文作品���,順著悠揚(yáng)的節(jié)奏體會(huì)其中的情操與意境�����。高三班上�����,孫老師教我們讀伊爾文的《李伯大夢》(Rip Van Winkle),課后我再三吟誦����,直到流暢無阻����,起了無窮。更有一次����,孫老師教到《李氏修辭學(xué)》��,我一讀到丁尼生的《夏洛之淑女》(The Lady of Shalott)這兩句:
And up down the people go����,
Gazing where the lilies blow……
(而行人上上下下地往來��,
凝望著是處有百合盛開)
便直覺必定是好詩�����,或許那時(shí)繆斯就進(jìn)駐在我的心底����。
至于中國的古典詩詞�,倒不是靠國文課本讀來,而是自己動(dòng)手去找各種選集���,向其中進(jìn)一步選擇自己鐘情的作者�;每天也曼聲吟誦���,一任其音調(diào)淪肌浹髓���,化為我自己的脈搏心律。當(dāng)時(shí)我對民初的新詩并不怎么佩服�,寧可取法乎上,向李白���、蘇軾去拜師習(xí)藝�。這一些,加上古文與舊小說�,對一位高中生說來,發(fā)軔已經(jīng)有余了���。在少年的天真自許里�,我隱隱覺得自己會(huì)成為詩人��,當(dāng)然沒料到詩途有如世途����,將如是其曲折而漫長,甚至到七十歲以后還在寫詩��。
青中的同學(xué)里下江人當(dāng)然不多�,四川同學(xué)里印象最難磨滅的就是吳顯恕。他雖是地主之子����,卻樸實(shí)自愛,全無紈袴惡習(xí)��,性情在爽直之中蘊(yùn)涵著詼諧���,說的四川俚語最逗我發(fā)噱��。在隆重而無趣的場合�����,例如紀(jì)念周會(huì)上����,那么肅靜無聲���,他會(huì)側(cè)向我的耳際幽幽傳來一句戲言�����,戳破臺(tái)上大言炎炎的謬處�����,令我要努力咬唇忍笑��。
他家里藏書不少���,線裝的古籍尤多�,常拿來校內(nèi)獻(xiàn)寶�����。課余我們常會(huì)并坐石階��,共讀《西廂記》����、《斷鴻零雁記》、《婉容詞》�,至于陶然忘饑。有一次他抱了一疊線裝書來校�����,神情有異����,將我拖去一隅,給我看一本“禁書”�。原來是大才子袁枚所寫的武則天宮闈秘史,床底之間如在眼前����,尤其露骨?�,F(xiàn)在回想起來��,這種文章袁枚是寫得出來的。當(dāng)時(shí)兩個(gè)高中男生��,對人道還半朦不懂�����,卻看得心驚肉跳���,深怕忽然被訓(xùn)導(dǎo)主任王芷湘破獲��,同榜開除���,身敗名裂。
又有一次�,他從家中夾來了一部巨型的商務(wù)版《英漢大辭典》,這回是公然拿給我共賞了����。這種巨著,連學(xué)校的圖書館也未得購藏���,我接手過來�,海闊天空,恣意豪翻了一陣�,真是大開了眼界。不久我當(dāng)眾考問班上的幾位高材生:“英文最長的字是什么�����?”大家搜索枯腸�,有人大叫了一聲說,“有了����,extraterritoriality!”我慢吞吞搖了搖頭說����,“不對,是floccinaucinihilipilification�!”說罷便攤開那本《英漢大辭典》,鄭重指正�。從此我挾洋自重,無事端端會(huì)把那部番邦秘笈夾在腋下���,施施然走過校園����,幻覺自己的博學(xué)頗有分量。
另外一位同學(xué)袁可嘉卻是下江人�����。我剛進(jìn)青中時(shí)�,他已經(jīng)在高二班����,還當(dāng)了全校軍訓(xùn)的大隊(duì)長,顯然是最有前途的高材生����。他有一種獨(dú)來獨(dú)往、超然自得的靈逸氣質(zhì)����,不但談吐斯文,而且英文顯然很好����,頗得師長賞識,同學(xué)敬佩���。
那時(shí)全校的寄宿生餐畢��,大隊(duì)長就要先自起立����,然后喝令全體同學(xué)“起立!”并轉(zhuǎn)身向訓(xùn)導(dǎo)主任行禮���,再喝令大家“解散”��!我初次離家住校��,吃飯又慢���,往往最后停筷��。袁大隊(duì)長憐我年幼�����,也就往往等我放琬����,才發(fā)“起立”之令��。事后他會(huì)走過來���,和顏悅色勸勉小學(xué)弟“要練習(xí)吃快一點(diǎn)”,使我既感且愧�。
有了這么一位溫厚儒雅的大學(xué)長,正好讓我見賢思齊���,就近親炙�����。不了正如古人所說,他終非“池中物”�����,只在青中借讀了一學(xué)期��,就輾轉(zhuǎn)考進(jìn)了全中國最好的學(xué)府“西南聯(lián)大”去了���。
后來袁可嘉自己卻得以親炙馮至與卞之琳等詩壇前輩�����,成為四十年代追隨艾略特�、奧登等主知詩風(fēng)的少壯前衛(wèi)。一九四五年抗戰(zhàn)勝利�,我也追隨青年會(huì)中學(xué)回到我的出生地南京,繼續(xù)讀完高三�。那時(shí)袁可嘉已成為知名的詩人兼學(xué)者,屢在朱光潛主編的《大公園》周刊上發(fā)表評論長文���,令小學(xué)弟不勝欽仰����。
五十二年后��,當(dāng)初在悅來場分手的兩位同學(xué)��,才在天翻地覆的戰(zhàn)爭與斗爭之余���,重逢于北京��。在巴山蜀水有緣相遇��,兩個(gè)烏發(fā)平頂?shù)纳倌觐^�����,都被無情的時(shí)光漂白了�,甚至要漂光了。
而當(dāng)年這位小學(xué)弟����,十歲時(shí)從古夜郎之國攀山入蜀,十七歲又穿三峽順流出川��,水不回頭人也不回頭��。直到半世紀(jì)后�����,子規(guī)不知啼過了幾遍�����,小學(xué)弟早就變成了老詩人����,才有緣從海外回川�����。但是這一次不是攀山南來,也并非順流東下�����,而是自空而降�,落地不是在嘉陵江口,而是在成都平原���。但愿下次有緣回川����,能重游悅來場那古鎮(zhèn)�����,來江邊的沙灘尋找����,有無那黑發(fā)少年草鞋的痕跡。